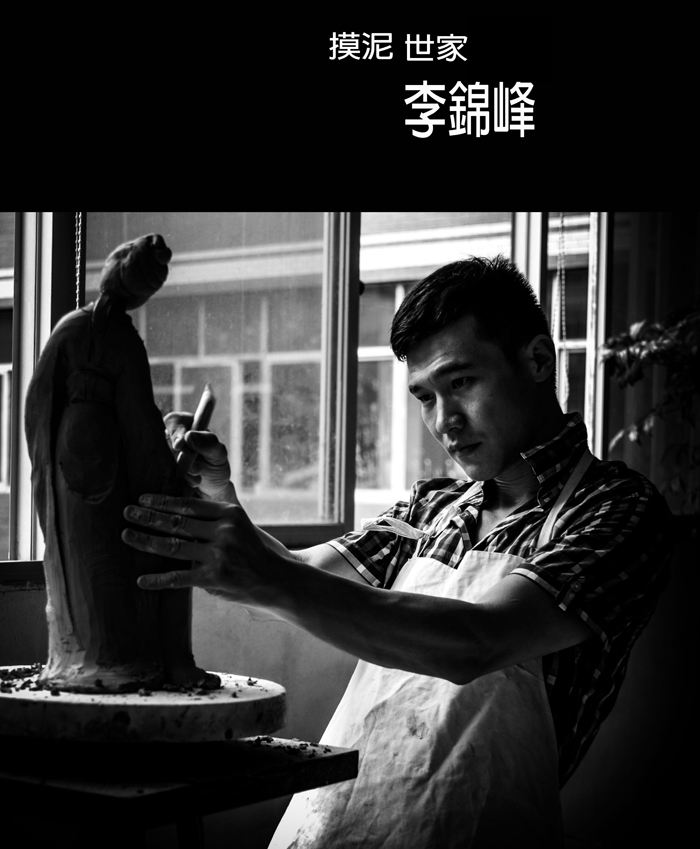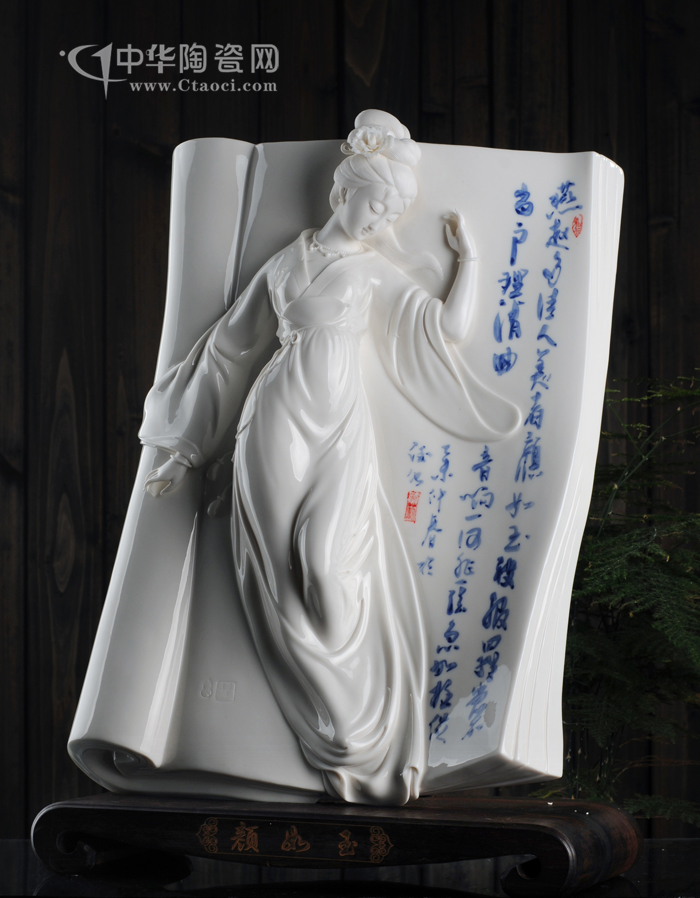見過德化陶瓷學院鄭振雷老師陶藝作品的人,無不感到輕松自然,那長度不一的泥條,粗獷的表面,讓人們置身于自然界中。
說實在的,在德化,很少人能邁出這一步,這一步跨越了八千多年的原始界線,拽一把陶泥壘成作品,把深層的含義疊起,把原始的人與自然和諧的真實作品連貫起來,這就是振雷陶藝作品創作的初衷。

正如振雷所說的那樣:要想使手工陶藝走如藝術殿堂,不能用太多的抽象和夸張,也要把藝術和手工自然的紋理疊加起來,才是真實的。陶藝創作不同于其他藝術作品,其中包含太多非人為控制因素,所謂謀事在人,成事在天,“十窯九不成”道出了陶藝創作的艱辛。
也正因為如此,陶藝創作吸引了那些充滿激情.堅韌不拔的陶藝家,用尋求“天人和一”的方式來傳達那些非物似物,非人像人的冥想之作。因此,我對振雷這樣的陶藝家及其作品懷有深深的虔敬之心。
當我走進振雷工作室———贏火陶藝工作室,視覺帶給心靈的感受猶如春雷滾滾逼近,仿佛聽到生命在泥土中回響。整個工作室設備比較簡陋:陶藝桌、雕塑架、一些自制的陶藝工具、一堆陶土而已。作品一個個老實的站在陶藝桌上,默默地注視著我的到來。振雷作品大都沒上釉或局部施釉,感覺像他本人如泥土一樣質樸一般。

振雷陶藝所采取的手工成型法之一 ——泥條成型,其特點是最大限度地發揮陶泥的可塑性及自由度,他在創作《風》的作品時,隨手拽一把泥搓成泥條,從一至十、從百到千等,每一根泥條仿佛都在言語,言它們存在的意義與價值。就是在成千上萬根盤筑泥條的同時,使我感受到了“九層之臺,起于壘土,千里之行始于足下”的偉大含義。
振雷的陶藝的最大特點是它的隨意自然,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泥料可塑性的自由度,可不受任何條件的限制,可按造型的需要,任意的將泥條旋轉、扭曲、擠壓、收縮等,成型后自然天成,絲毫無人工雕琢之感。這一特點,足以保證和色釉渾然一體,不僅如此,千變萬化的色釉一旦得到恰當應用,不但能增強泥條盤筑陶藝的色彩冷暖視覺效果,達到黑、白、灰的層次美感,同時,泥條的干裂,穿插的紋理,凸凹的肌理更使色釉得以變化莫測,巧奪天工。作者在創作《風》系列時,旨在表現風的感覺,而表面形體的凸凹變化,又給觀者以“物”的懸念,而這個“物”會讓你聯想多多,給人一種無法定位的感性認識。而這種認識恰就是振雷陶藝作品耐看的價值所在。
《戰服》的創作采取了泥板成型技法,用粗礦的泥板卷成,外加紐扣,簡潔的形式,體現古代戰服簡易的裝束,上面長了小草,寓意著沒有了戰爭,人們渴望和平。

《原始足跡》則采取傳統花瓶來制作,運用絞胎技法進行裝飾,產生自然的紋理,仿佛看到原始人類勞作的場面,口徑采取手工卷泥板成型,給人以親近感。既保留了傳統器型又滲入了現代設計理念,給人以雅俗共賞之感。
火與土是陶的語言,它的產生是中華民族的驕傲。現代陶藝是先民智慧的沉淀。沒有生命的泥土,注入了思想,便有了靈魂;高溫煅燒后,也許會出現奇跡。陶,便有了它的神秘性。聽其聲、觀其色、聞其味,細細感受傳統文化的輝煌燦爛。振雷陶藝給我們帶來了身臨其境之感。
陶藝是陶瓷藝術派生出來的一種新的藝術形式。
陶藝制作吸收了現代繪畫和現代雕塑的造型手段和技法,現代陶藝是從古代陶藝中發展起來的,但不是傳統陶藝的重復,雖然在泥條盤筑,拉坯制作,拼接等工藝與古代有相同之處,卻是現代藝術觀念的產物。傳統陶藝造型講究規則平衡,器皿的口,頸,肩,腹,足底,兩邊的大小,長短,高低的結構要求一致,輪廓線以弧行為主,繪畫線條要精細,釉面要光潔,不能出現變形,斑點等缺陷,燒成后的開裂,起泡等都被視為廢品,這可以說是人們對古代陶瓷藝術的認識。而現代陶藝的造型,裝飾隨意性強,通過扭曲、翻卷、拼貼等技法,既有抽象特征,又有自然形體的韻味,在欣賞視覺中給人們一種聯想的空間。返樸歸真是時代的呼聲,現代陶藝便更具有時代性。
在人們對陶瓷藝術審美多元化的今天,返樸歸真、回歸自然的文化意識悄然在人們的心中埋下深深的種子,而振雷這種陶藝作品象是春天的雨水,必將催出人們對陶藝認識的幼芽,愿其陶藝作品開出更加燦爛的花朵,成為陶藝界一朵絢麗的奇葩。